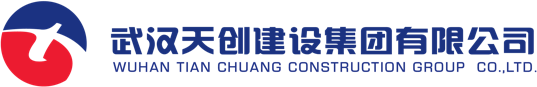在这步履匆匆的时代,少有人捧书而坐,在闲隙间感受书香。君不见低头一族,手机刷屏之神速,游戏微信QQ,在地铁上,在公交站台,在任何一个可站可坐可躺的地方,都有着庞大的低头一族。而我还是喜欢书香。
成年人的忙碌不可用天来形容,是用小时和分钟来堆积。成年人能够承受的压力也不可用量来形容,如果用一种颜色来表示压力量,那么一片片的灰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尽管如此,我依然在临睡前的晚上,手捧一本季老的《牛棚杂忆》,哪怕只读上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,磕睡虫便不约而至,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
白天再多的纷繁,随着我翻开书的任意一刻起,便将一切抛向了天外,这是属于我的世界。
八零后没有经历过牛棚,家里长辈也没有经历过这些,那个时代对于我来说,一切都是陌生的。那些狂热的激进的苦难的情感,在季老的笔下变成从容。而我们生活中的工作压力也好吃苦耐劳也罢,在那段岁月面前,不值牛毛。下面跟我一起翻开书:
可是我当时的任务是看门,当门房。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?我当时还是“分子”—不知道是什么“分子”—,我头上还戴着“帽子”—也不知是些什么“帽子”—,反正沉甸甸的,我能感觉得到。但是,“天无绝人之路”,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“妥善”的办法。《罗摩衍那》原文是诗体,我坚持要把它译成诗,不是古体诗,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。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,我也要押韵。但也不是旧韵,而是今天口语的韵。归纳起来,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“押韵的顺口溜。”就是“顺口溜”吧,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,也是不容易的。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,仔细阅读原文,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。第二天早晨,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,在上班以后看门、传呼电话、收发信件的间隙中,把散文改成诗,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。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,揣在口袋里。闲坐无事,就拿了出来,推敲,琢磨。我眼瞪虚空,心悬诗中。决不会有任何人—除非他是神仙—知道我是在干什么。自谓乐在其中,不知身在门房,头戴重冠了。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—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,其他的花也在盛开,姹紫嫣红,好一派大好春光。
这是命不保夕的季羡林,在牛棚中的一个小小片段。苦难之于他仿佛于外星人,他依然幽默,守住自己一方小小的天地。
你没有理由抱怨,更没有理由不热爱生活。请你收起手机,打开书,一起感知人生,深呼吸,甩掉沉重,开启新的美好的一天。 (徐敏/文)